当太阳行至黄经105度,小暑以“温风至”的信号叩响盛夏之门。
何谓小暑?夹在夏至与大暑间,总感觉少些存在感。然而,它绝非夏日的简单延续,而是自然时序中关键的“热量”转折点。与夏至“昼晷已云极”的白昼极限不同,小暑标志着暑热从“积蓄”迈向“爆发”。在成都平原,6月的高温天数已刷新纪录,而7月的小暑更像是酷暑的“前奏”。与大暑“上蒸下煮”的湿热相比,此时湿度虽未达顶峰,但烈日的锋芒已不容小觑。农作物进入灌浆结实的关键期,万物在炽热中淬炼出独特的生存智慧。
小暑还藏着什么?古人与“天”偕行的生存哲学。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以“温风至,蟋蟀居壁,鹰始鸷”勾勒小暑物候特征,三者构成应对高温的智慧。当温风取代春风的和煦,蟋蟀放弃野外暴晒转而迁居屋檐墙缝阴凉处,而老鹰则逆势而上,在更高远的清凉气旋中盘旋捕猎。这种“趋利避害”的智慧,同样体现在人类活动中:四川农村至今保留“小暑晒伏”的传统,农户选正午烈日翻晒谷物,以高温灭杀虫卵,确保储存安全;同时将棉被、衣物晾晒于竹竿,让阳光穿透纤维,驱散梅雨残留的湿气。热浪滚滚,却成了生活的助力。
小暑炙烤年复一年,人们对暑热的饮食应对也奇招迭出。小暑时节讲究吃“新”,将农事节律与饮食调节巧妙结合。用新米做饭熬粥,既能防暑又能调理肠胃。与北方“头伏饺子二伏面,三伏烙饼摊鸡蛋”的主食变换不同,四川人更注重“清凉泻火”:泡仔姜的酸辣刺激唾液分泌,冰粉凉虾爽口直达脾胃,淋上海椒油的凉面加速散热。这些川味美食通过视觉和味觉的双重作用,演绎出独特的消暑之道。
清爽解暑的双河凉糕 摄影/C视觉 牟一平
文人笔下的小暑是怎样一种精神意境?“温风”“蝉鸣”“蟋蟀”皆成序章。唐代诗人元稹在《小暑六月节》中写“倏忽温风至,因循小暑来”,“倏忽”“因循”写出时令流转的紧迫;南宋诗人赵师秀笔下的“黄梅时节家家雨,青草池塘处处蛙”,则捕捉了小暑“出梅”的气候特征。四川诗人流沙河的诗歌《就是那一只蟋蟀》,描述了在某个夏日夜晚想起田间一堆堆的草垛、竹笼,想起呼灯篱落。市井生活场景附上小暑韵律,暑热不可避,人心却能静。
伴随小暑而来的,还有不容忽视的地质灾害风险。四川盆地独特的盆周山地地形,在小暑时节常形成“昼晴夜雨”的气候模式:白天的持续高温加剧空气对流,夜间极易形成强降雨,由此引发滑坡、泥石流等灾害。古人虽不具备现代监测技术,却通过长期观察物候总结出了一套预警智慧。农谚“小暑一声雷,倒转做黄梅”,正是通过小暑节气的雷电现象预判异常降水。这种“以物候观天象”的传统智慧,如今仍在基层防灾实践中发挥作用,让古老的气候知识流传到现在。
当我们在空调房里吃着冰镇西瓜时,或许还能从“晒伏”的谷物香气、“尝新”的米粒清甜中,感受到小暑这个节气穿越千年的文化脉搏。它不仅是日历上的一个标记,更是中华民族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存密码,在阳光下持续书写着生命的顽强与灵动。
本期话题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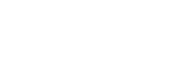



评论 0
还没有添加任何评论,快去APP中抢沙发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