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为首批“四川十大历史名人”之一的西汉辞赋家扬雄,其在成都的故宅、子云亭、洗墨池等遗迹,已在岁月长河中陆续湮没,唯留文字记载供后人追忆。
如今,消失八十余年的扬雄洗墨池在旧址重现。路人纷纷驻足,或疑惑张望,或恍然颔首,或凭吊怀古,或肃然瞻仰。在这市井喧闹中,一方古迹悄然氤氲着千年文脉,让匆匆行人不禁驻足,感受脚下这片土地沉淀的文明气息。
从成都青龙街转入青龙巷,沿铂金城向北步行至尽头,一堵红墙与一座朱漆四脚木牌楼便映入眼帘。二者之间,一块横卧的巨石上,“扬雄洗墨池”五个阴刻红字格外醒目。穿过题有“子云巷”的牌楼,左侧墙脚处,便是那方复现的洗墨池。
这处新修的洗墨池不过两三平方米,被假山环抱,带着鲜明的现代气息。在寸土寸金的繁华商圈,如此复建虽难复原貌,却让沉睡的文化记忆重新苏醒——它承载的,是一座城市对文脉的守望。
相传,这方池塘曾是扬雄读书习字后濯笔涤砚之处。随着扬雄声名远播,这方寻常水池也被赋予了文化灵魂,“墨池”之名流传千年,成为成都重要的历史印记。其实,不仅扬雄,蜀地许多文人墨客都留下过洗墨池的佳话——江油李白、资阳王褒、资中赵雄、绵竹张栻……一方方墨池,沉淀着巴蜀大地的文脉绵长。
但细究起来,成都青龙巷这处洗墨池并非扬雄真迹。要解开这个谜团,还得从扬雄当年在成都的居所说起……
扬雄曾在成都居住多年,但他究竟住在何处?
《太平寰宇记》记载:“子云宅在少城西南角,一名草玄堂。”少城西南角即古市桥附近,大约位于今通惠门以东、下同仁路一带,靠近西胜街和古郫江水道。北宋学者何涉在《墨池准易堂记》中进一步明确:“(扬雄)有宅一区,在锦官西郭隘巷,著书,墨池在焉。”这里的“锦官西郭”即当时的成都县西郊。
盛唐时期,诗人岑参曾寻访扬雄故宅并作《扬雄草玄台》一诗,可惜未提及具体位置。他在游览青龙街龙女祠时所作的《龙女祠》诗中,同样未见扬雄故宅的记载。晚唐学者郑暐在《蜀记》中则明确指出,扬雄故宅(草玄亭)位于青龙街龙堤池畔的龙女祠旁,而龙堤池即当时的洗墨池。
历史变迁往往出人意料。晚唐时期高骈修筑罗城时,扬雄故宅和洗墨池被迫迁移,易地重建于青龙街中兴寺内。这种因城市建设导致古迹迁移的情况,在成都历史上并不鲜见。由此可以确定,青龙街的扬雄遗迹实为晚唐时期迁建而来。
位于成都市青龙街的子云亭 图据方志四川(1934年庄学本摄 杨显峰 提供)
北宋庆历七年(1047年),成都府知府文适听闻中兴寺僧人怀信讲述扬雄故宅和洗墨池的往事,有意修复。派人查看旧址时,发现扬雄故宅已改名为龙女堂,洗墨池也早已荒废。次年,高惟几在旧址恢复洗墨池,修建准易堂,并在堂内绘制扬雄画像。他在洗墨池中央垒起台地,建造解嘲亭,还修建了用于宴会的场所——吐凤轩,种植奇花异树,使这里成为一处风景清幽的胜地。
南宋末年,准易堂毁于战火。元朝初年,镇守四川的都元帅纽璘奏请朝廷,将文翁石室、扬雄墨池、杜甫草堂列入学宫体系,并自费修建三所书院,墨池书院由此诞生。可惜在元末明初的战乱中,书院再遭破坏。
明朝弘治时期,蜀王府承奉宋景重修书院,成都府知府耿定力在洗墨池边立碑纪念。当时的洗墨池有多大?蜀王朱申鑿在视察后写下的《墨池怀古》诗中描述:“半亩方塘湛碧天,子云遗迹尚依然。”按此推算,面积约相当于现代标准篮球场的80%,规模不小。
明末清初,扬雄故宅、洗墨池等再次遭到严重破坏。清康熙二年(1663年),成都府知府冀应雄组织人力疏浚洗墨池,修建草玄亭、木桥,并刻石记载此事。
光绪三十一年(1905年),成都学堂成立时,洗墨池面积尚大,池中横跨一座长桥,桥上和岸边都种有柳树,池边还有子云亭……此后池水面积不断缩小,最终只剩一个小水塘,后来被填平改作操场。
清光绪年间《四川省城街道图》中的洗墨池位于青龙街,而子云亭旧址在成都县署内,今天的署前街。 图据金牛区方志办
如今,扬雄洗墨池以新的姿态重现蓉城。这不仅是对历史记忆的修复,更是成都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实践。从北宋到当下,一代代成都人守护文化根脉的努力,恰如那池中清水,虽历经岁月冲刷,却始终清澈如初。
本期话题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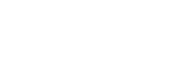



评论 0
还没有添加任何评论,快去APP中抢沙发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