恩阳古镇,自公元525年梁武帝置义阳郡起,至今仍保留着18条古街巷、2处明清戏楼。当晨光穿透万寿宫戏楼的雕花窗棂,老茶客们已坐在八仙桌旁,茶碗里香气四溢,戏台上好戏连台。这种“商贾聚则戏班兴,百姓爱则戏脉延”的生态,让恩阳“戏窝子”的名号经久不衰。
川剧表演 张学金/摄
商脉与戏脉的千年缠绵
恩阳“戏窝子”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源于其作为“米仓古道第一镇”、川东北水陆码头的商贸繁华带来的文化交融,以及民间对戏曲的深度热爱与世代传承。
米仓古道上的声腔密码
恩阳的戏曲基因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的巴人歌舞。恩阳作为“米仓古道第一镇”,成为南北声腔的“文化熔炉”。早在元明时期,恩阳就出现了皮影戏、端公戏、庆坛戏等传统戏曲形式。元至正年间,江西商人沿水路入川,在万寿宫修筑戏楼,引入弋阳腔;明洪武年间,陕西商人于三圣宫建秦腔班社,与本土巴渝舞融合形成“弹戏+道情”的独特唱腔;清康熙年间“湖广填四川”移民潮中,湖北渔鼓、湖南花鼓与川北灯戏在禹王宫戏楼碰撞出新的艺术火花。这种“五方杂处”的声腔融合,在乾隆年间达到鼎盛——万寿宫戏台现存“一曲阳春唤醒今古梦”对联,正是商贸文化与戏曲艺术共生的最佳注脚。
会馆制度下的戏曲生态
恩阳的会馆不仅是商人联谊的场所,更是戏曲创新的实验室。江西万寿宫的“堂会制度”规定,每年春分、秋分必须举办“迎神戏”,戏班需表演弋阳腔《目连救母》;湖广禹王宫则创立“对台戏”传统,两支戏班同时在戏楼两侧竞演,观众用银簪投选优胜者。这种“以戏会友”的机制催生出独特的戏曲生态:清光绪年间,麻石垭艺人陈登翰组建首个川剧班社,其创立的“蛇形步”身段体系被载入《川剧艺术通论》;民国时期,十二家茶馆形成“一街一戏”景观,同乐园大众社在大众茶社开创“川剧座唱+讲圣谕”的复合表演形式,被《巴中县志》称为“川北场镇之冠”。
恩阳古镇历史上主要会馆有:万寿宫(江西会馆)、禹王宫(湖广会馆)、三圣宫(陕西会馆)、龙母宫(广东会馆)、天后宫(湖北会馆)、新场禹王宫(湖南会馆)、武圣宫(山西会馆)、老城禹王宫(福建会馆)。恩阳古镇历史上八大戏楼为:回龙场财神庙戏楼、姜市街王爷庙戏楼、文治寨下文昌阁戏楼、老米市巷禹王宫戏楼、关山万寿宫戏楼、石匣子沟图关戏楼、中咀上白云寺戏楼、河东新场禹王宫戏楼。
革命烽火中的戏曲新生
1933年红军进驻恩阳后,将戏曲作为宣传工具,改编传统剧目(如川剧《打土豪》),将“分田分地真快活”唱词融入“二黄腔”传统曲牌,既保留民众熟悉的戏曲形式,又注入革命内容,让戏曲从“娱乐消遣”延伸到“思想传播”,这种改造模式与延安平剧研究院的革命戏曲实践形成跨时空呼应,被《中国革命戏曲史》称为“基层戏曲改革的典范”,不仅丰富了戏曲的表现形式,也提高了戏曲的社会功能,使戏曲更加贴近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斗争。
新中国成立后的戏曲发展
1954年成立恩阳川剧团,创排《斩巴蛇》《四下河南》等剧目,二十世纪60年代并入巴中川剧团,2013年恩阳区重建川剧艺术团,年均演出80余场。被称为“川剧界的莎士比亚”黄吉安,曾在恩阳采风6年,创作了20多部川剧剧本。从恩阳走出“梅花奖得主”肖德美、李乔松等蜚声中外的川剧大师。二十世纪60年代成立的花丛女子川剧团,以全女性阵容演绎《背鞭》等剧目,曾受张爱萍将军作诗赞誉:“春色满园乐融融,百花丛中一点红,女子组团演乡戏,发扬传统创新风”。
多元声腔的活态基因库
恩阳的戏曲文化并非单一剧种,而是以本土剧种为核心、融合周边戏曲元素的“多元集合”(地理基因、移民基因、红色基因)。这种多元性体现了恩阳作为水陆码头的开放包容特性、湖广填四川带来的多元声腔融合、革命时期戏曲改造的独特路径,也反映了恩阳人民兼收并蓄的文化心态。
河派川剧:
水韵里的五腔交响
作为川剧五大流派中唯一以“河”命名的分支,恩阳河派川剧融合高腔、弹戏、胡琴、昆曲、灯调五大声腔,形成“一戏多腔”的独特范式。其代表剧目《四下河南》巧妙融入“巴山背二哥”号子,唱腔中既有陕西商人的陕腔道白,又有本土方言的诙谐表达。河派川剧独创“弹戏+道情”混唱,如在《斩巴蛇》中发展出“蛇形步”身段体系(引《川剧艺术通论》)。恩阳地方川戏《牡丹灯》第七场“惊魂索命”中,陕西商人唱腔道白纯用陕腔:“一早去赶恩阳河,卖了棉烟买馍馍,唱几句梆子稳住脚……”这种“移步不换形”的创新智慧,在当代创作中延续——《挂印知县》采用“外聘演员+本土演员”的协作模式,既保持艺术水准又凸显地域特色,获首届四川艺术节“最佳剧目奖”后,更进京登上长安大剧院舞台。
川北灯戏:
田埂上的喜剧哲学
恩阳灯戏是川北灯戏的重要组成部分,源于民间“花灯”,通常只有2-3个角色,剧情简短、曲调轻快,多反映农村生活,道具也很简单,常用花灯、手帕,常在街头、院坝演出,俗称“坝坝戏”,也称之为“农民戏”“喜乐神”“鼓乐神”。2006年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川北灯戏,在恩阳形成独特的体系。其经典剧目《闹菜园》融入“鸡公车推粮”舞蹈,《送京娘》则以“三步两回头”的表演程式展现川北农民的幽默智慧。近年来,创新剧目《李扯火脱贫》通过“坝坝戏”形式,将脱贫攻坚故事融入灯戏表演,获“乡村振兴·美丽家园”工程一等奖;2025年新创川北灯戏《饭碗》获国家艺术基金立项资助。
傩戏双璧:
端公戏与爨坛戏
端公戏起源于元明时期,与民间信仰紧密关联,因由“端公”(巫师)主持祭祀仪式而得名。其表演融合傩祭、跳端公、庆坛等元素,早期为驱邪纳吉的仪式性戏剧,后逐渐融入世俗娱乐内容。端公戏的“正戏”与“耍戏”二元结构,体现了巫术仪式与世俗娱乐的辩证关系。《大战红山》中戴面具扮诸神的表演,与《耍傩傩》中融入顺口溜的娱乐片段,形成“神圣-世俗”的张力空间。爨坛戏(学名“傩戏”)起源于元明时期,流行于巴中、南江等川东北地区,2022年被列为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。其名称源于古代祭祀时烟火升腾的场景,核心功能为驱邪纳福与世俗娱乐。爨坛戏则以“正坛”与“耍坛”的区分,展现从法事仪式到喜剧表演的演变轨迹。如《赵公求寿》《龙神记》包含开坛、驱鬼、祈福等流程;《孟姜女》《包公审城隍》常搭配“上刀梯”“过火坑”等特技,既保留了原始祭祀的神秘性,又增添了现代观众的观赏性。
恩阳皮影戏:
光影中的指尖戏曲艺术
川北皮影戏是借助光影演绎的“指尖戏曲”,唱腔多沿用川剧高腔,影人用牛皮雕刻而成,色彩艳丽、制作精美。旧时恩阳皮影戏班常走街串巷演出,是孩童最爱的“移动戏台”,经典片段多选自《封神榜》《三国演义》。皮影戏在恩阳有着悠久的历史,早在元明时期,恩阳就出现了皮影戏。皮影戏表演需要艺人同时掌握演唱、操纵和乐器伴奏等多种技能,是一门综合艺术。
恩阳皮影戏在长期发展过程中,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地方特色。近年来,恩阳区通过建立传习基地、开展进校园活动等方式,使这一古老艺术得以延续和发展。
文旅融合的传承创新
恩阳的戏曲传承并非停留在“怀旧”,而是通过“保护+创新+普及”的组合拳,让“戏窝子”真正“有戏可看、有人会演、有人爱听”。
空间营造:
从戏楼到演艺之城
恩阳的文旅融合战略以“空间再生”为突破口,建设演艺之城。万寿宫整体提升改造后,设置“民俗剧场”与“川东北川剧艺术博物馆”,形成“演-展-研”一体化空间。新建的800平方米河派川剧戏楼,可容纳2000余名观众,其飞檐斗拱的建筑风格既保留了明清会馆的韵味,又融入了现代声光电技术。依托大栈房、起凤廊桥、登科公园等,创建演艺场地100余处。其中,万寿宫每年演出超300场。
传播创新:
从茶馆到数字云端
恩阳区实施“戏聚古镇”,推出“演艺+茶艺”,坚持老戏新演、老调新唱,年表演《变脸》等戏剧300余场次。“戏进校园”工程每年开展60余场活动,形成教师、学生、家长“三维共促”机制。文创开发方面,“戏饭礼”系列将川剧元素融入蓝印花布、竹编等传统技艺,年开发12类5000余件产品,其“红梅玉簪”文创产品更成为游客争相购买的“网红”单品。数字传播方面,通过抖音等网络平台发布的《恩阳戏窝子》系列短视频,让年轻群体在“云看戏”中感受戏曲魅力。
游客在万寿宫欣赏文艺节目
精品引领:
从经典剧目到新剧创编
恩阳区挖掘恩阳籍肖德美等名人事迹和民俗文化,创编川剧《挂印知县》《玉簪记》,曲艺《打亲家》《黄荆树》等精品10余部。明代传奇《玉簪记》“复活”——这部四川近40年未曾上演的川剧“八大记”之一,经与肖德美工作室联合重排打磨,让古老艺术以时尚姿态走进日常生活。恩阳还深化文化惠民,建强演艺人才队伍,创排《中华龙抬头》等精品折子戏30余部,亮相“中华龙舟大赛”“成都世运会”,以“大戏精品”带动“小戏小品”蓬勃发展。
《恩阳传说》表演
产业融合:
从夜游到文创经济
恩阳区坚持文旅融合,迭代升级夜游演艺《恩阳船说》,创编提升《打亲家》《放河灯》等文艺精品,举办全国“村晚”“年在恩阳”“广场舞展演”“龙舟赛”“古镇夜游季”等活动,激活文旅市场。《恩阳船说》夜游项目投资2亿元,采用真人表演与声光电技术结合,讲述宋代恩阳夫妻的家国故事,成为激活古镇旅游经济的“引爆点”。该项目不仅带动了周边民宿、餐饮等产业,更催生出“戏曲+旅游”的衍生业态。文创经济方面,通过“非遗工坊”模式,将皮影雕刻、川剧服饰制作等传统技艺转化为旅游商品,既增加居民收入,又实现非遗的活态传承。特别值得关注的是“戏窝子”IP的开发,通过“戏饭礼”“红梅玉簪”等品牌,构建起从文化符号到经济价值的转化链条。
恩阳的“戏窝子”文化,既是一部流动的川东北戏曲史诗,更是一幅活态的文旅融合画卷。在这里,商脉与戏脉缠绵千年,传统与创新交相辉映,保护与发展并行不悖。随着文旅融合战略的深入推进,这座千年古镇必将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璀璨的光芒,让“戏窝子”的戏脉永远绵延,让川剧的韵味永远流传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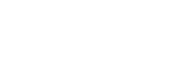



评论 0
还没有添加任何评论,快去APP中抢沙发吧!